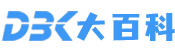为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阅读前请辛苦点下“关注”。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关于青色
之所以要探讨青色与《千里江山图》,不仅是因为《千里江山图》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中集大成的青绿山水,也在乎于青色浓郁的文化情结。而《千里江山图》是将其视觉审美化后相对完整的表现。
什么是青色?我们通常会想到“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或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前者出自荀子《劝学》中对提取靛青这种颜料的描述,后者则是毛泽东对雨后彩虹的描绘。
17世纪,牛顿从太阳光中分离出七种可见光,把波长范围在420?450nm的颜色称为青色或者靛色。
19世纪歌德指出牛顿的色彩光学只是光的物理现象,从视觉色彩的层面,人作为观察者与自然这个被观察对象是不应分割的,注重了色彩在心理上的含义。
因而,我们可以有效的感知青色是某一种蓝色,但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蓝,深蓝还是浅蓝?是偏暖偏绿,还是偏冷偏紫?严格地说,对青色的色彩界定至今都是相交才模糊的。
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以严谨的哲学逻辑揭示了颜色的相对性,指出颜色存在于一个系统的“颜色空间”中,脱离了其他颜色环境单独就一种颜色而论是没有意义的。
维特根斯坦的理论给我们以启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种颜色有着不同的定义和象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时代,同一种颜色也有着不同的界定与意义。
要探讨青色在《千里江山图》中的表现,就要把“青色”最终放在宋朝的大环境里面来讨论。广义来讲,“青色”不只是颜料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下,青色有着丰富的色彩内涵。
从“青”字的造字字形上可以了解其最初的来源与意义:最早出现的“青”字单字记载的金文“青”,上部是“生”下部为“丹”。
《说文解字》中:“青,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象然。”而《说文解字?生部》解释:“生,进也。象艹木生出土上。”在《释名?释采帛》中也有相关论述:“青,生也。象物生时色也。”
由此可推断,“青色”指五行中的东方之色,与草木初生时的颜色有关。《诗经》中的“绿竹青青”、“其叶青青”,《楚辞》中的“秋兰兮青青”、“青黄杂糅”等等,都反映了“青色”就是指草木生长时所呈现的颜色—绿色。
张清常在《汉语的颜色词(大纲)》中提出:“从先秦开始,它(青)就兼指蓝、绿、黑三色。”此外,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中“青”字笺的部分提出“丹沙、石青之类,凡产于石者皆为之丹。盖丹为总名,故青从丹生声,其本义为石之青者。引伸之,凡物之青色皆日青矣。”
由此,“青”从“丹”字旁,在造字之初就蕴含了“石性”,且是偏向草木初生之色的某种矿石。在古代常用的矿物染料中,孔雀石和蓝铜矿极有可能是所谓的“石之青”。
有趣的是,孔雀石与蓝铜矿其实是同一种的矿石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两种表现形态:当自然环境中的孔雀石处于干燥、密闭且二氧化碳充足的条件时,就会生成蓝铜矿;若条件改变,则又会变成孔雀石,二者之间的转化是可逆的。
此两种矿物所提取出的颜色,蓝的称为“石青”,绿的叫做“石绿”。因而,青色本身的色彩属性就包含了蓝色与绿色的两大色系,笔者后文中所探讨的“青色”之于《千里江山图》实则是就青绿两种颜色展开的。
对自然的向往与敬意,于惟恍惟惚中取其象,敷其自然山石中亘古不变的孔雀石绿与宝蓝空青,以笔墨落于丝絹。用自然的馈赠来描绘自然,妙得而后迁想,的确不失为一件妙事。
在传统中国画颜料的范畴里,青色包含了花青和石青两大主要色系。花青是水色,从植物中提取颜料。石青是石色,属矿物颜料。在石青试制过程中,有生成头青、二青、三青、四青等青色。
颗粒大,沉在下层的为头青,色深、饱和度高。依次向上,浮在最上层的色最浅,饱和度最低,通常为四青。此外,画史中提及的青颜色还有空青、曾青、扁青、标青、大青等。第二节青色成为文化符号的根源青色作为“五色”之一,自古都坐拥着色彩的优越感。
秦朝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穿青色袍;汉代的丞相和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三府官最为崇贵;明清时期文武百官皆着青色官袍。全唐诗中青色系的色彩词汇的使用多达16500多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色彩意象。
像杜甫的“一行白鹭上青天”,李白的“且放白鹿青崖间”,王维的“怀素在青山”等等。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发展至宋代以“千峰翠色”著称的青瓷,其最具代表的汝窑青瓷,其天青色釉蓝而不艳,灰而不暗,青而不翠,美而不妖。
“捩翠融青穆色新”、“轻施薄冰盛绿云”。将青色的色彩审美推向了制高点。自唐朝兴起,经历了五代的沉寂后在宋代迎来高光时刻的的青绿山水画,更坚定了青色的色彩自信。
青色的高频现象贯穿在政治、文学、美术、工艺等领域。选择青色作为山水的主色调的原因,或者说偏好青色的文化情绪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首先,我们先天有着对青色敏感的生理优势。视觉器官的生理构造对色彩的鉴别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拥有灰色、碧蓝色瞳孔的民族,在辨别光谱中的蓝一一绿暗色一端较为困难。相比较而言,黑褐色的瞳孔具备更理想的调节外来光线的能力。
因而,我们中华民族在辨别青色方面较为敏感,能更细致的捕捉其丰富而微妙的变化,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
其次,社会生产力对颜色偏好的影响。长久以来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民族的色彩审美。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就的,而它的境况归根结底是受它的生产状况和生产关系制约的。
采集和农耕的生产方式使我们长期环抱在青山碧水、郁郁葱葱的环境中,色彩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受到青色长期的浸染,已经无法割舍得积淀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了。因而才会有“青萝拂行衣”的寻常亲昵以及“绿树村边合”的自然而然。
再者,外来文化对民族色彩感知的冲击。西方佛教绘画传入前,中国绘画主要遵从五彩彰施的设色方式,画面大多以暖色调为主。汉唐时期,印度佛教文化大面积入主中原。青绿色系的壁画不胜枚举。
像西魏时期莫高窟第285窟主室南壁的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其山头石青山脚石绿预示了之后青绿山水赋色的基本形态。这种西来的冷调带着明显近东民族的色彩认知。
由于长期生存在黄沙漫漫的隔壁环境中,周围除了灰黄色的天空就是明黄色的骄阳。人们对水源、对生命的绿洲有着本能的渴望。因而,民族意识中对色彩的补齐成为内在需求。用清冷的蓝绿色调可以有效遏制极目望去大面积黄褐色的色彩失倾。
所以当我们看到像克孜尔千佛洞这样环视皆是青绿色的石窟时,或许可以理解其中饱含的渴望。最后,道家思想崇尚青玄色的色彩观念。
北宋是道家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徽宗时期大量修建道观,大规模印制道家典籍,道释绘画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道教是东方之教,而青色属东方,是生的象征。
老子等道家先哲所秉持的观念,不仅推崇和践履阴柔之水所具备的道德品质,还主张一种“以柔克刚”的人生策略。
老子的“上善若水”就是在推崇这种不争却锵锵,能容万物也能攻坚强者的品质。也许是种暗合,水阴柔的特性表现在色调上也多为青色的冷调:素湍碧潭、水天一色等。
在心理体验上,青色具有淡泊、空灵、悠远、宁寂之感,与中国山水中讲究的清逸、淡远的境界是相吻合的。